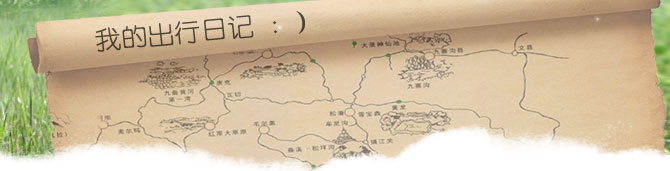昨天到乌镇去了。
之所以决定去,只是想把围困的自己释放一下,希望可以从此改变,透透气。
绝对典型的小镇子,就到发黑的小阁楼,都有木板搭乘,黑瓦的顶,真正临水而居,只见游人,不见镇里的人。那些人呢?
当然也依然有人住在那里,因为有盛开的花,有水边晾晒的衣服,还有偶尔袅袅炊烟。就这样沉静的一座小镇子,青石板的路,我以为我会感动,可是没有,心如止水。也许游人太多,我的心被挤出人群之外了吧。
信步走,推开一扇虚掩的门,一位八旬老太太友好的指了一个角落说:“厕所在那边。”我却一下子几乎流泪,大概所有推开这扇门的人都是为了这个目的吧!可我只是想看看她的生活。她正在桌边吃饭,白米饭,豆腐和蛋,并不坏。她十分老丑,仿佛从未青春过,屋里的一切都黑乎乎的有股异味,墙上挂着一副大大的遗照。当然,那应该是她的爱人——曾经的爱人,早已离去了的爱人。我无法心如止水了,也许他们就这样在这个镇子里相识相爱了,默默走着走着,就失散在阴阳两界了。老人十分安详友好,我却异常辛酸。从那个小屋出来后,我的游览不再纯粹,我认真的感受小镇所承载的一代代人的情感,那些和这个镇子同龄的人,那些至死未能走出的人。
前面一排小屋的门牌吸引了我:
“应家桥岸上33号”
不知为什么,感觉这里面应该有个很轰轰烈烈的故事,人们都忘了,而小镇记得。屋子里早已无人居住,我依然执著的透过门缝,企图看个究竟,但看不看都一样——因为什么也没有。
一扇门上贴着一张纸,提醒游客:回来不走原路,过三座桥,前途光明。于是随心地过了三座桥。
就是这样,一旦知道了,就会做,宿命吗?
路过矛盾的故居,去连一点看的兴趣都没有,原本我也不是为它而来的,为谁?为自己吧!为许许多多平凡的生命。
一座高高的戏台上,一个女人出来唱《还披风》,粗糙沙哑的嗓音,粗壮的身段,五彩缤纷的一张脸盘,很多人有意无意的在台下驻足,不知是以怎样的心态看着。我问朋友:“她快乐吗?”
“不知道,但愿她快乐!”
我特意走近台下,看她的手,很糙,由此可知她亦不年轻了。这样的活着,好吗?
有农妇在弄蚕茧,把茧子抛进热水,翻开套在手指上,把里面的蚕蛹丢到一旁,很丑陋,还有一股臊味,这就是丝绸的最初来源了。
也许很多东西还是不求甚解的好,怪不得那座道观前有这样一句话:人有千真,天则一算。让我又想到那句:人类一思考,上帝就发笑。当然,也许我的领悟完全错位,但无妨。
这个镇子上也许有一些特产,如米酒、印花布、木雕、手织布之类,但上海似乎也有很多,这种想法破坏了所有感觉,“现代”使很多东西不伦不类,连收藏的必要也没有。
不是我世俗吧?!
就这样走完了这个镇子,没有太多感觉,我亦不敢祈求在一刹那沉淀。
离开了。
并非一无所获,并非有很多收获,这也就是正常吧,我并未能走出自己。
只是沉静下来了,很静。
我很明白那句话:“我痛的想哭,却傻傻的笑”
不再笑了,因为想静下来抚平心中一点点的褶痕,给自己重新开始的机会。
昨天,经过乌镇,经过自己。
作者:laixilj